作者简介:
王东东,1983年生于河南杞县。出版专著《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6),诗集《空椅子》(Red Hen Press,2013),《云》(阳光出版社,2015)。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并任华语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深度叙事、智慧抒情与精神戏剧
——序《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
王东东
罗兰·巴特在定义虚无主义时引用了尼采的话:“支配的目标贬值了。”巴特攻击说:“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或许是潜伏着的:以某种方式隐于习俗、陈词滥调、表面的终极性之内。”在考虑新世纪诗歌这个大题目时,将巴特的话作为提醒不无裨益。首先要确定新世纪诗歌的前史或参照,也就是1990年代的诗歌具有哪些特征?在精神上,后者是怀疑主义的,尤其相对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而言;在技术和风格上,则可以概括为有限度的叙事或克制叙述,对于“民间派”是白描(口语)叙事,对于“知识分子派”则为反讽叙事,而实际上二者有彼此混淆甚至合流的危险;因而在文学类型上1990年代诗歌实则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很大影响,甚至具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品格,但这一点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忽视,不像在小说领域那么高调。新世纪诗歌呈现出的基本面貌,现在可以说就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虽然离1990年代还不够远,但它的各种品质其实已初露端倪并呼之欲出。
李之平主编的这本《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具有一种“奇异的阵容”,也许会让某些人咋舌,但并不能简单归之于编者的人脉、眼量或识见,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编选都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探究的是编选体现的客观内容,以及和“无限的客观”相关联或比照时的逻辑。实际上,相对于前一段时间出版的《五人诗选》,这本书编者的“雄心的独断”要少得多,如果不是更为“无原则的宽容”的话;当然无论什么样的选本都可理解为一种因缘际会,毕竟它都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在总体中认识个体”甚至“在个体中塑造总体”的机会;我们也应该同情那个随摘随丢的猴子,要入宝山而不空归不能说是贪心;做一个诗歌导游而能自个儿任性游赏一回也不错:这甚至也是我敢于动笔的最终动机。实际上我们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对当代诗歌的编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诗歌文化在公共空间的展示。不仅有益于被选中的个体,更无损于当代诗歌的总体。
这本诗选中有深刻介入九十年代诗歌的诗人,如臧棣、桑克,也有第三代诗人如韩东、杨黎,还有一直处在“边缘”却不容小觑的实验型诗人,如余怒,以及一直热衷于发明并传播概念的诗人,如李少君、谭克修、周瑟瑟,甚至一反出道时的“三级艳星”形象而专攻严肃文艺片的“下半身诗人”——不过这个词现在应该废弃了——也就是沈浩波,但谁又能断定沈浩波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个被误会的小清新的汤唯呢?另有四位女诗人,李轻松、冯宴、安琪、从容,所占比重仍然太小,编者虽为女性似乎也显得有点重男轻女,更有在新世纪初暂露头角的诗人,如聂广友、津渡、育邦、苏野、曾纪虎、魔头贝贝、泉子、孙慧峰……他们不少是70后诗人,这是令人欣慰的;以年庚而论,这本诗选全部是60后和70后,其实80后诗人在新世纪能自成一家者并不少,一个也不能入选,这又是令人遗憾的。但就整体而言,仍能看到这本书对年轻诗人的推重,如果将70后也看成年轻诗人的话。无论怎样吧,从这片偶然织就的当代诗歌锦绣,总能看出变革中的纹路、图样抑或模式。
如果要比较新世纪诗歌与九十年代诗歌,不一定按照进化论思维来进行,正如对于“百年新诗是否成熟?”——这个题目是否熟滥,取决于论者能否提出具有新意的理想模型。也有必要以理想模型来取代进化思维。17世纪伟大的批评家叶燮在《原诗》中提出过一套诗歌理论,理、事、情三要素在诗歌中的有机融合。然而,在实践中,这三者必有偏至。叶燮自己也解释说:“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论证。叶燮十分注重诗歌语言与逻辑语言或曰诗与哲学的差异:“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就整体而言,叶燮所谓的“理”并不能简单归之于中国诗歌的禅意或禅理,虽然他受到禅宗哲学的影响。叶燮的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理事情三元素说,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围绕诗歌的语言、美学和文化程式,囊括了诗歌的技术、艺术和道术的层面。对于现代诗歌,我们也可以说,它要求事境、情境和理境三者的统一,但这只是理想,何况在实践中又每有偏至,而现在每一个元素都面临重新塑造。以理境而论,揣摩“五四”巨人的设想,对个人来说是(心灵的)自由境界,对群体而言则为民主精神。然而,这样高远的诗学理想却并非不能为当代人所理解:
窗外,一只鸟的鸣叫,如此放肆
从高音到低音,从短音到长音
其间的转换挪移,迅捷得
出乎我的意料,像是在嘲讽我贫乏的韵律学
又像是一种炫技。似乎它意识到了自己的轻佻
某一个瞬间,它重新回到沉寂的立法院
随后是更多的鸟鸣,穿过方言的郊区涌向我的耳膜
而那多出来的一滴,是否代表了美学的剩余
——蒋立波《民主的诗学》
虽然这里更多是对民主的内在化以及“美学观照”。新诗史上备受珍视的“智性抒情”,其实也体现出情理融合的理想,能够见出诗人对新诗“哲理品格”的期待。其成果不一定是落入窠臼或传统的哲理诗,而更多在于对丰富生活内容的包容。九十年代诗人看重的叙述,其初衷也无非如此,意在一种正视生活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陷于叙事与抒情的意气之争实在没有必要。诗歌中的叙事毕竟不同于小说叙事。而小说家韩东则在诗里说:
字和词不再折磨我
我也不再折磨语言
——韩东《这些年》
对语言即抱持一种通达态度,看来重要的还在于对生活的发现。这两句诗似乎是其早年诗话“诗到语言为止”的发展,诗歌似乎是一个浓稠的语言地带或语言沼泽,而现在,诗人要重新向生活回归,这时即使生活的表面也让人觉得可喜欲泣,仿佛尤利西斯经历了语言的流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韩东先知先觉的诗歌观念,似乎比他的诗歌作品影响更大。他最近很少就诗歌发言,但从他的作品仍能看到当代诗歌的一个转机:生活的真理,必将受到诗歌的青睐,虽然后者总是自以为占有了诗歌的真理。而技术上的发明,所谓深度叙事,也应该朝向真理性内容。与韩东同样的喟叹,甚至同样的觉悟,更年轻的诗人有着不同的表达:
我不能系好精神的安全带
一种载体的悲伤,我停不下来
我的骄傲在于“道”
在于“道”成为悲伤,成为语言
——苏野《孟郊》
这能经受住凝视的意识将归属何处?
不是你,也不是我。
它没有必要的源头性——
受惑于可转接的情境,如那
交通之域,存有之域,
生生之域。
——曾纪虎《红蓼引2》
甚至更为细腻,更多层次感,也展示出更多存在的褶皱。苏野注意到了语言和存在的分歧,语言意志的一意孤行也会加深世界的支离破碎,曾纪虎则模仿了“凝视的意识”,带有现象学色彩的“意向性”,但他更多注意到了语言和存在的对称,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克服语言的困惑。就整体而言,年轻诗人既具有推崇“语言本体”的语言哲学素养——这为他们沉浸于“语言的欢乐”提供了必要支持,又能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思考诗歌问题,后一点甚至更为值得期待,因为它意味着个人真正走进历史的可能。智性抒情的修为应该包括对语言的领悟和对人类历史生活的领悟这两个方面。现在来看,中国诗歌的智性抒情形象还要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合力完成,自然也包括女诗人的作品。
那只最初的青苹果,却依然生动
它隐没在叶色里的模样多像我的生活
我生活里斑斓的色调自古就适于我
——李轻松
亲爱的,你用几个世纪的仇恨
在身体上挖出这黑色的陷阱
如此狂野地引诱我此生一起陷入
亲爱的,我多么渴望
你黑色的伤疤
被我凝视时,成为我
——从容《第一次见你褪去衣服后的疤》
李青松的“最初的青苹果”是一个绝佳的象征,它暗示着女性生命、语言和诗艺的统一,女性生命的疼痛被投入到语言中,并在语言中获得救赎。从容的诗歌则具有一种戏剧化的激情,她甚至想象自己是一个异性,获得声音的面具并与自我展开对话,在更高的意义上完成自我认知和自我升华。新世纪女诗人的作品已超出自白派的范围而表露出更多对话气质和“超性别”的智慧。
这是我抛弃了两千多年的道德与仁义,抱着江水吞没的石凳
从水底、从出海口走上沙滩,执意用沙子
建造佛塔的黄昏,消弭于海水
巨大的手掌,顷刻间翻覆于无形的黄昏。
——津渡《黄昏的绘像》
在罗列不休的黄昏意象中,一个被传统压抑或竟“冤死”的人终于出场,以一种诡异、坚决执拗而又刚烈的方式,只有求生意志本身才具有这样的形式,从水底走向江岸并建造一座塔,这个人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宗教精神,一种救赎精神,一种形而上学精神,一种植根于“无”的精神,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然和神的面前的不管什么时代和国度的人,以及这种人的激情、疑虑、罕见的得志和难以想象的悲惨,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诗的主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精神戏剧;无论如何,贵族时代已然远去;中国二十世纪就已经是一个民众时代;而只有经历民主品味的淬炼,我们才能回归汉语那醇美、柔和的贵族精神。而新诗的一个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据说总是处在对立关系中的传统与现代,也许会在这一个新的世纪和解。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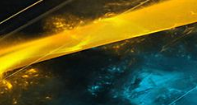
评论列表